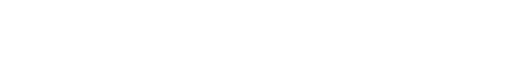新海派及新海派中的艺术管理
New “Hai Pai” (Shanghai-Style) Culture
and Its Art Management
作者简介
董峰(1972— ),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管理学术史、艺术组织社会学、艺术场馆规划与运营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摘 要
无论从艺术参与人口还是艺术消费市场抑或艺术国际影响,都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以新海派为代表的上海艺术始终呈现领先于全国的蓬勃发展态势。基于从海派艺术到新海派艺术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本文初步梳理了特定时段与特定场域下艺术、管理与教育交织互动、双向同构的逻辑关系及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中国自主知识生产”的学术自觉为视角和进路,初步探讨了作为标识性自主原创概念新海派的文化蕴涵与教育承载,提出并阐述与新海派艺术伴生的艺术管理及其教育的新命题和新话语,并试图以此为描述和解释上海艺术发展的轨迹与动力提供理论工具。本文认为,上海地区文化建设的兴盛局面与其艺术管理及教育的蓬勃发展密切关联,这是上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且不应该被忽视的特征。但这一点是否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
新海派;艺术生产端;艺术消费端;作为目标的艺术管理;作为手段的艺术管理;艺术管理高等教育
20多年前一个被称作“新海派”的名词屡被提及,而它所指向的文化实践在更早的 40年前就开始了。走到今天,“新海派”之概念在美术、戏剧、文学、设计、建筑、家具等领域声名鹊起,因为其突破了“海派”概念对新时代文艺无法充分且准确言说的局限,故而反响热烈。①如,2020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提出“新海派”的创作理念和办学主张,试图在象牙塔内外激活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美术文脉与文化使命,颇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②的复兴意味;又如,从2022年起《上海艺术评论》开设“新海派文化艺术研究”专栏,希望更多的学者和身处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参与到讨论中来,加深对新时代海派文化特征的认知,研判新时代海派艺术的走向,共同探讨它对城市文化精神的传续与发扬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所产生的作用。与此前后,以新海派为主题或主旨的书画展览、文艺评论和学术研讨纷纷登场,新海派俨然成为阐释上海艺术区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主流话语,引起了学者、艺术家、教师、官员等不同群体的广泛关注。在此契机下,基于“上海城市文化特质核心表达”[1]这一学术立场,从艺术、管理与教育交织互动、双向同构的学术框架探讨新海派艺术发展的轨迹和动力,无疑是值得特别书写的一篇大文章。
01
新海派艺术的坚守与蝶变
毋庸置疑,没有海派艺术自然就没有新海派,而海派艺术无论由谁,从哪里开始书写,都是中国近代艺术史绕不开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上海1843年开埠,作为最早开始接触并融入全球化的口岸之地,这里也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祥之地。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上海始终处于全球化浪潮之中,历来人口流动频繁,商业经济繁荣,市民群体活跃,形成了杂糅江南文化和西洋文化、荟萃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且流光溢彩、变动不居的海派文化。然而文化毕竟是一条河,或者说它像一座桥,链接历史和未来的两端。所以现实中谈新海派既不能把海派抛在脑后,也不能死抱着海派不放,正确的方式是将二者视为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既要守住传统,又须突出原创。照此说来,海派艺术和新海派自有其生生不息的道理和路数。
作为海派艺术独特而又典型代表的美术领域即是如此。清末民初,一批在传统之上坚持开拓创新的画家被上海兴起的工商业及城市文化所吸引,纷纷聚集于此并创立了一种非常具有地域风格的绘画,“海派”美术随之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表述,用以表征迎合市场的商业性、大众性、娱乐性以及敢于突破陈规的笔墨语言和风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美术领域在上海蓬勃发展的态势,使得“海派”这一概念难以继续标识它的整体面貌和深层结构,更不说新时代上海文化建设面临扎根人民、满足市场、服务国家、走向世界的新任务了,因此,这一时期的海派美术逐步被大家称作“新海派”。
与作为固定术语的“海派美术”是一个生成式开放性的概念一样,新海派的含义、特征与范畴依然处在讨论之中。文化学者郑崇选阐发新海派文化的内涵和新海派艺术的价值,[1]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分析新海派美术的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2]策展人马琳解释新海派展览的市民趣味和市场逻辑,[3]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连同一些研讨会上不少人对新海派美术的即兴发言,可以认为大家的讨论在四个维度—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地域风格,时代品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叙述框架。而海派和新海派恰是在这一叙述框架中经过观照比较,各自的内涵与边界才能得以逐步清晰。进言之,新海派在海派基础之上于内部构成及外部网络方面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审美特质和文化生态。其实,于上海而言,美术之外的戏曲、音乐、舞蹈、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存续与发展皆是如此。
第一,绘画与市民关系的新变化。大家都说海派绘画特点比较多,以至于它的标识性不够强,但都市意识和市民观念肯定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今天新海派绘画依然如此,这一点我们在冠名新海派的展览里看得非常清楚,比如在创作题材、绘画语言上更强调上海城市化进程在画家的艺术世界投下的巨大的心理光影,以及对他们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但新海派与早期海派在对待绘画与市民的关系上已大不相同了。早期海派中,市民往往是绘画所要表达的对象以及其创作的素材、体裁而已,当然市民也是绘画市场的消费主体,但不管怎么样,在那时,画家是画家、作品是作品、市民是市民,它们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然而今天在社会美育、社区艺术等观念的浸润下,新海派绘画走出画室、美术馆等传统栖息地,走进了街区、商场、村社等新空间,和市民的关系紧密地融为一体了。而新海派绘画的创作手段,包括因科技赋能而添加更多沉浸体验的展陈方式,使市民除了作为创作对象的一部分,有时候也是创作主体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绘画作品的建构者和生产者,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的观看者和消费者。当然,今天这一现象在全国美术界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探索和表现,但应该说新海派美术在打破传统绘画边界,向生活渗透与向生产延伸方面做得更加自觉且系统,也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
第二,绘画与美术院系关系的新变化。根据史料统计,从1910年到1949年上海陆续成立19家新式美术专科学校,当然有些机构说是学校其实不过是社会培训班。[4]但无论如何,早期上海滩专业美术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与海派美术的兴起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民国早期新式美术专科学校是海派美术的大本营和主阵地,而海派美术则是新式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素材,两者是同频共振的复合体。今天,依然可以说上海的专业美术院系是新海派的大本营和主阵地,也可以说新海派美术是专业美术教育的重要课程和教材;进一步说,上大美术学院、上戏舞美系,以及华师、上师的美术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如此阵容撑起了上海美术事业的一片天,即使北京、重庆、南京、杭州等全国美术重镇的优秀画家移师上海,专业美术院系往往是沪漂的第一站。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作为新海派大本营和主阵地的上海专业美术院系已与早期海派有着天壤之别了。民国时期,全国成立的美术专科学校总共39家,而上海地区在数量上可谓占据半壁江山。[4]反观今天,整个上海的专业美术(设计)院系约略20 家,而全国远远超过500家,上海的数据不足全国5%。[5]依借高等教育经典理论来说,一个地区在整体意义上其大学的规模、结构与其质量、效益具有一致性,如果一个地区的大学没有足够的规模以及适当的结构则难以形成充分的质量和基本的效益。因此说, 在绘画与美术院系关系上,新海派与早期海派不可同日而语。
深入分析还发现,早期美术学校是早期海派美术生产端的提供者。具体言之,那时成立的美术学校首先是海派画家的供养者,其次是海派绘画新人的培养者,再次是绘画作品的生产者,其四是美术思潮的推动者。也就是说美术学校提供了海派美术生产的平台和阵地(当然包括绘画题材与风格的推陈出新)。但发展到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专业美术院系除了依然是新海派美术生产端的提供者,它还成为美术消费端的推动者。换句话说,现在专业美术院系在培养画家、输出作品、促发思潮,以及直接组织或间接参与各类艺术活动,比如美术评论、美术科研和美术智库之外,同时举办课程、开设专业, 承担培养各类艺术管理者—策展人、投资人、拍卖师,与书画鉴定、修复、经营人员—的职责,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担负培育、引领美术消费者的任务。这些事项越来越成为推动上海美术事业发展更加重要的力量。
02
新海派艺术中社会性力量的形成
统计数据显示③,上海是全国艺术场馆座次及艺术展演场次数量最多、密度最高的城市。而且在数据之外,上海艺术发展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这一地位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且不说更早的,单就从改革开放算起,上海艺术发展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始终走在全国前面,且始终葆有与时俱进的纵深性和海纳百川的广阔度—鲜明的新海派艺术审美趣味与文化特质。
究其原因,除了依循艺术的发展总是在坚守与蝶变的交织中曲折渐进而非断崖突变这一条自身规律外,还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外部社会性因素的深刻影响。其一,上海持续经历着由生产主导型城市向消费主导型城市的系列转变,在比较宽松的政治舆论环境和比较活跃的经济商业氛围的基础上,孕育着比较繁荣的文化消费市场,文化消费逐步升级。其二,上海相继提出“开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文化品牌”,尤其在2017年提出构建亚洲演艺之都、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等文化发展战略,④为推动海派文化向更高水平、更大目标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其三,由上述两点变化引发而来的,居于艺术生产与消费体系中介地位的艺术管理逐步由被动的传统经验化走向自觉的现代学科化,这一点更为直接和重要,当然艺术管理的变化也是新海派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艺术管理并不新奇,早在两千多年前,艺术管理的全部问题—计划、组织、职员安置、监督指导和控制各种管理职能在艺术领域的普遍运用—就已为人知晓。同样, 艺术管理的社会作用也并不新奇,哪怕是一两千年前,举凡集体性、规模化的艺术活动,无不需要运用管理手段作为分工与协调的工具并以此解决效率与效益的根本问题。在今天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管理,不仅关注公共、非营利艺术组织,而且涉及私立、商业的艺术实体,同时则把由创意经济衍生的艺术科技、艺术金融以及非遗传承、公共文化服务、跨文化艺术交流等更为宏阔的时代课题纳入进来。特别在上海这样丰富复杂的艺术市场环境中,艺术发展须臾离不开学科化艺术管理的直接推动和间接促进。
艺术管理对上海艺术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表现为涌现了大量艺术市场中介或平台。美术领域,与展览和拍卖相关的各类中介组织或平台大量涌现,运用策划、筹资、营销等管理职能,一方面挑选并服务艺术家,另一方面培育并拓展观众(客户),从而大大促进了上海画廊、拍卖行和艺术博览会三级艺术品市场完整体系的形成与高质量发展。演艺领域,同样由各类中介组织或平台于国际范围内在艺术生产和消费之间架起双向互通的桥梁,确保了上海演出场次和票房数的连年双增长。由此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地区演艺市场活跃、艺术品市场发达,除了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因素,也许是因为这个地区拥有比较多的艺术家、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也许并非如此,甚至观众都不一定以本地区为主,但是这个地区一定拥有足够的艺术管理者以及艺术经营机构,否则整合艺术资源、激活艺术需求、培育消费市场就无从谈起。
于上海而言,正是一大批策展人、制作人、营销及评论人员也从海内外聚集上海, 与本土各类管理人才一道,使这里的艺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成为艺术发展国际化、市场化进程重要的一部分。
在市场之外新海派的文化实践同时表明,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全国之所以最为发达、完善,也是因为这里拥有足够的科班出身的、可以称作“文化义工”⑤的艺术管理者,他们以自下而上的自治方式和志愿方式推动了社区艺术、市民艺术的发展,而这正是艺术市场、艺术商业繁荣的前提。
当然,直接推动新海派发展的艺术管理本身也发生了质变,它不再是原来海派中的艺术管理了,开始由被动的传统经验化走向自觉的现代学科化。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管理兴起于艺术中介机构市场竞争的加剧与商业经验的积累,其发展则伴随着管理知识的广泛应用与艺术事务分工的精细,由此艺术管理专业教育应运而生。艺术管理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和生产知识,为艺术发展提供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艺术管理对上海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上海艺术管理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上间接地反映出来。换言之, 要了解上海艺术管理的形态、机理、作用也可以从其教育进程与类别中一窥究竟。
1982年,上海市文化局委托上海戏曲学校举办“艺术管理专修班”,迈出全国在职干部专攻艺术管理第一步(紫雪,1988)。1986年,上海市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决定在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二工大分别举办文化管理研究生班、本科班、专修班,标志着文化管理人才培养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并且在全国最早形成专、本、硕三级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龚心瀚,1988)。1989年之后, 限于特殊原因,这股办学力量曾有过短暂的消沉与低迷,但乘着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很快在上海复兴起来。1993年,原国家教委批复上海交大创办文化艺术管理本科专业,使之成为全国艺术管理专业办学第一家(刘玉珠,2002)。2016年,经过二十余年以专业方向为形式的教学探索和积累,上海戏剧学院率先成为全国首批成功申报艺术管理特设专业的两所高校之一,目前已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董峰,2018)……这一系列创举,[6]表明当代上海艺术管理教育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
目前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的上海高校分别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四家,开设艺术管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也是这四家,而冠名艺术管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则有上戏和上大两家。不直接冠名艺术管理,但在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等层面涉及艺术管理人才培养的高校有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等多家。这些院校的艺术管理教育虽名称不一、类型多样且个性鲜明,但它们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专业建设理念及方式,无疑与新海派的文化品质有着内在一致性,很好地体现了“新海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风貌。因此,上海艺术管理教育适应甚至超越了上海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且各项办学指标遥遥领先于全国。
03
新海派中艺术管理与教育的变革
在艺术史上,所谓“派”指的就是学派、流派或门派。中外艺术史虽然派别林立, 且其概念之内涵与边界尚无确指,不过约定俗成的特征认识总是有的,比如要有领军人物以及代表性的艺术主张,要有群体阵容以及共同遵循的创作观念,要有经典的艺术作品和创作成果,要有传承的路径以及传播的范围。如此看来,艺术派别其实蕴涵着今天比较流行的学科范式或学术共同体等概念的意味。然而有趣的是,西方艺术史多以思想或思潮分门划类,而中国多以地域或朝代划派立宗,当然中国以地域或朝代为艺术划派无疑也包含了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等基调,隐含着特定的艺术思想或思潮。
不管清末民初兴起的“海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海派”,因为各自都拥有与时代相契合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范畴,所以两者分别作为艺术之派、话语之派和学术之派是当之无愧的。不只如此,新海派与艺术管理及其教育呈现互动同构关系,相互提供了外部需求也彼此创造了内部的发展空间,自然比海派更胜一筹。同时也促使与新海派伴生的艺术管理及其教育随之发生新的变异,形成新的面向。
众所周知,海派艺术从兴起那刻起,就是由在地生产端推动,众多志趣相投的艺术家聚集上海,与在地艺术家一起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艺术类别,而那时的艺术消费端是受生产端支配的,且本地市场明显大于外域市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新海派艺术则使消费端走向前台,同时消费端由在地市场扩展为全球市场,并带动了在地生产端的发展,更是吸引了全球生产端在此汇聚。由此就使上海艺术市场的国际消费端远远大于其在地生产端,这一点与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艺术生产—消费体系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艺术生产竞争加剧,由艺术生产到艺术消费的中间环节不断延长且日趋复杂。从此, 艺术的权威不能代替管理的权威,艺术发展必经艺术管理之统筹成为新的规则。而艺术管理本身也在不同群体的争议、辩解中不断损益、代谢、嬗变、拓展和深化。
不论是基于管理职能在艺术领域的具体应用,还是将艺术管理视作艺术与文化生产、销售和消费汇集处的社会活动,其根本在于整合、协同各类艺术力量以把展览和演出完美地呈现给最大规模的观众。[7]此类外显的、单一的艺术管理—把艺术作为资源、把管理作为手段,以达成艺术活动之目标—今天可以称之为“作为目标的艺术管理”(оf)。然而因为新海派基于时代的坚守与蝶变,使其由单一侧重生产端到兼顾生产和消费端的转向,最终带来新海派艺术管理在“作为目标的艺术管理”(оf)之外又新生一种内隐的、系统的艺术管理—把艺术管理本身作为乡村建设、社区治理、非遗传承等社会活动的载体或手段,来实现艺术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弘扬—相应地今天可以称之为“作为手段的艺术管理”(by)。由此艺术管理形成了“作为目标的”和“作为手段的”多样取向和完整内涵,而这无疑是由与商业社会及商业文化相对应的市民社会及市民文化所形塑,也是为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民主自治机制所需要。
基于艺术实践的生长性、丰富性以及概念内部共识稳定的局限性,“新海派”艺术的提出策略性地采取简单的时间序列逻辑,但在与海派艺术的区别和差异的明确性上依然具有强大的阐释能力。而从新海派语境下艺术管理内涵与外延、价值与影响的分析中,则不难发现上海地区的艺术发展与其艺术管理密切关联。加深对上海艺术发展这一重要且不应该被忽视的特征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多元文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今天,上海正在努力建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⑥、江南文化,奋力谱写历史文脉的当代华章,然而具有上海文化特质的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也是与海派文化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动关系之中。海派文化不等于上海文化,但最能代表上海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表达。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上海艺术的发展不管采取什么独特的思路和方式,都离不开处于新海派文化中不断变革的艺术管理的支撑和引领。换言之,一种蕴涵在新海派文化中的新时代艺术管理,将以一种新的逻辑和机制推动上海文化艺术高质量发展。第一,坚持“双向驱动”,把作为目标的艺术管理和作为手段的艺术管理的两种力量协同起来,这两种力量的区分既不同于艺术事业和产业的差异,也不同于营利和非营利性艺术的区别,它是现代社会新的文化机制,既服务文化市场又贡献市民社会。第二,坚持“两端发力”,以新海派文化优势为主旨,持续发展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剧乃至数字艺术、时尚艺术、娱乐艺术,使其艺术生产端始终走在时代前面,走在全国前面,同时大力推动艺术消费端的发展,升级场景、注重体验、强调参与,培育新质文化生产力。第三,坚持“三头并举”,在艺术生态营造上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打造更高水准的文化地标集群、更高人气的文化交流舞台、更高能级的文化交易平台,以“在地出品,全球共享”来定义“上海文化” 并使之成为城市神韵魅力的核心标识。
然而,与新海派伴生的艺术管理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其支撑性的主体力量即艺术管理教育却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其一,规模偏小。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艺术学门类设置一个一级学科和六大专业学位类别,在一级学科里“艺术管理”列为13大学科范围(类似于二级学科)之一,且排在第二位,而六大专业类别的培养范围都涵盖“管理”领域。由上海艺术管理教育现有规模观之,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上海艺术管理教育很难说适应了国家艺术学科专业布局的需要。其二,结构失衡。上海现有艺术管理教育主要集中在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领域, 而在视觉艺术和舞蹈、戏曲等领域明显滞后,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视觉艺术领域,央美、国美、川美、鲁美的艺术管理专业都是二级学院建制,而上海仅有的上海大学艺术管理教育还是二级学院下设的专业系或教研室,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新海派艺术随时代的坚守与蝶变必然需要艺术管理及其教育相应的继承与发展,因此,理应在现有基础之上取长补短,去粗取精,以新海派的心力推动艺术管理教育的更新与再造。第一,推动提供艺术生产端与推动艺术消费端的专业艺术院系统筹发展,切实改变目前主要以前者为主的教育结构。第二,推动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影视等各门类艺术管理教育均衡发展,更好地适应上海文艺百花园的生态布局。第三,推动具体门类艺术管理教育的学科和专业类别协调发展,既培养懂实践的艺术管理研究者,更培养懂理论的艺术管理实践者,让他们在文化艺术发展中发挥各自应有的类别作用。
04
结 语
新时代海派艺术从承继、熔铸到新变、发展的曲折反复过程,为提出新海派的概念以及揭示其中蕴涵的新命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和文本基础,同时新海派概念的提出以及其中新命题的揭示又对描述和解释新时代上海艺术发展的整体面貌和深层结构提供认知框架和言说方式。一般而言,拥有文化领域新概念与其说是话语主体意图掌握并传播话语权的有意为之,但更由蕴含在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文化资源的市场力量、学术力量决定。具体言之,具有文化标识性意义的“新海派”是由以“上海文创50条”⑦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战略催生、文化市场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共同塑造的文化新概念。与新海派相呼应的演艺新空间、美术新空间、阅读新空间等文化新概念在上海的涌现,其逻辑皆是如此。而这些陆续涌现的新概念俨然成为上海文化建设一道独特景观,作为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具体表现,它改变了很长一段时间像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文化遗产等新概念或新命题主要由外国学者提出的尴尬。可以说,艺术“新海派”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传播意味着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中的典型示范与担当,该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文化艺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顺应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的制度诉求,对文化概念进行分层、分类和归并、转换,以揭示其实践和理论的概念簇群及其关系,由此提炼能够在国内外通用的原创标识性概念,继而自主建构系统性理论,正是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取胜之道。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新海派艺术首先是地域文化,虽然它在上海地区的蓬勃发展与其艺术管理及教育的蓬勃发展密切关联,但这一点是否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注 释
① “海派”一词之出典依然待考,一般认为与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有关,目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今天上海文化主体依然被称为“海派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上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地方文化流派。而根据学界普遍的认知,新海派则是海派文化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表述。
②此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③上海市文旅局网站,
https://whlyj.sh.gov.cn/zfxxgknb/20240201/1adfaa39a1d64c2d8e4977c034 fb0258.html.访问时间2023-09-12.
④分别参见:《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府文件。
⑤文化义工,又称文化志愿者,即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文艺技能等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和帮助的人。他们是志愿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志愿者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志愿者的专业性更强,强调公益文化艺术服务。
⑥四这里的海派文化即是新海派文化,之所以未用“新”字,是由于政策统一表述所致。
⑦即2017年由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上海文创50条”。
参考文献
[1] 郑崇选.新海派艺术的文化语境与理论重构[J].上海艺术评论,2022(01): 9-11.
[2] 毛时安.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海派国画[J].美术, 2018(12): 96-97+95.
[3] 马琳.从“风自海上”到“无问西东”—“新海派”与未来美术教育[J].美术, 2022(10): 96-99.
[4] 郑工.演进与运动: 1876—1976中国美术的转型[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2:39.
[5] 董占军,王亚楠.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艺术教育的机遇与挑战[J].艺术管理(中英文), 2023(03): 29-39.
[6] 董峰.论艺术管理教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 236.
[7] 董峰.对艺术管理的解读[J].艺术探索, 2010(06): 32-36.
本文原载于《上海视觉》 2025年第1期 P39-45